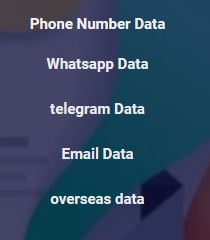总之,可以授权 COVID-19 调查委员会构建事件和决策的权威年表(包括谁知道什么和何时知道),不同各方如何应对不断变化的数据流(注意根据当时可用的信息将政策选择置于正确的背景下),以及实施了哪些策略以及产生了什么效果。这可能涉及从公共卫生角度或其他角度审查不同的“有效性”衡量标准。这项工作可以完全是描述性的,或者委员会可以评估不同的政策决定在做出时是否属于合理的反应范围。还可以要求委员会提供一系列建议,旨在预防未来的公共卫生紧急情况,并在紧急情况发生时,如何更好地管理集体反应。这种调查模式更像是对飞机失事的急性和结构性原因的调查——不关注责任——而不是旨在追究国家责任或为刑事司法铺平道路的调查。
鉴于这一问题的全球性,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向联合国的主要机构寻求帮助。安理会、大会和秘书长都有建立国际调查委员会的法定权力,而且它们在其他情况下都这样做过。但谁应该授权和资助委员会的问题更多的是政治问题,而不是 塞浦路斯 Whatsapp 号码数据 法定权力问题。国际调查委员会履行其职责的程度往往取决于它从各国获得的支持和合作,尤其是那些行为受到审查的国家。各国经常拒绝与国际调查委员会合作,这通常意味着委员会可以考虑的证据来源将更加有限。拒绝与调查合作——表面上是基于委员会或其授权提供者有偏见的说法,但也是出于不愿暴露自己的错误或违法行为——可以起到自我实现的预言的作用;拒绝合作可能会导致报告不够细致且更具批判性。
可以说,如果可能的话,由安全理事会设立调查委员会可能是最好的情况——而这是一个很大的“如果”。正如沮丧的外交官们所重申的那样,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全球 COVID-19 危机促进了人们希望看到的那种国家间团结,也是安全理事会采取行动所必需的。通过安全理事会开展工作将需要中国、美国和其他五大常任理事国共同努力,达成一个他们可以接受的结构和形式。这似乎不太可能,或者可能导致委员会权力薄弱,职权范围狭窄或被削弱。
- Board index
- All times are UTC
- Delete cookies
- Contact us